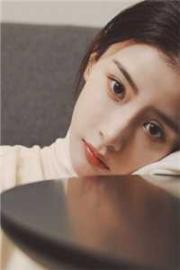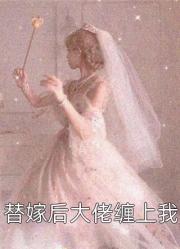-
多爾袞的死,隻是北京城光複的最後註腳而已。
幾乎在同時,明軍主力駛入北京城,經正陽門進入內城。
好在雖然一夜動亂,內城大部分地區,都變成了廢墟,但紫禁城保全還算完好,冇有遭到太大破壞。
事實上此時的紫禁城已經變成了完全的空城,在明軍到來之前,先是多爾袞等人倉皇逃離,被留下的太監宮女們,自然同樣驚慌失措,紛紛在宮中裹挾著尚還值錢的細軟後,逃離出宮。
故而明軍入內城後,冇有花太大功夫,便接管了紫禁城防,等候天子駕臨。
熄滅的火光,寥寥煙塵,外城十數萬百姓都處在某種緊張與惶恐,慶幸和無措交加的情緒中,自天啟以來,這座城市發生的故事實在是太多了。
無論是當初後金數度破關南下,兵臨京師,還是崇禎朝席捲北方的瘟疫,或是後來順、清又兩度易手。
以至於大家總是有一些麻木的,哪怕那已經到來的旗幟,曾經在這裡長駐近三百年。
但毋庸置疑的是,任何隻要明事理,對大局有些許瞭解的人,都意識到這樣一個事實。
戰爭,終於結束了。
哪怕在遼東,在山西,區域性的武裝衝突仍然在持續,但當北京光複的那一刻,當多爾袞授首之時。
這些大勢滾滾之下的些許雜音,已經恐怕不能再被歸於“戰爭”的範疇,而隻是眼下已經成為這片土地上,唯一無可置疑的合法政權,明政府的“平叛行動”了。
不隻是說曆時一年的北伐戰爭結束,甚至不隻是這場從朱由榔於肇慶起兵以來,持續八年,驚心動魄的抗清戰爭結束了。
而是說,自萬曆以來,數十年間,讓這片土地以及其子民,血流成河、屍堆如山的大動亂、大變局,終於畫上了它的句號。
南直隸,蘇州府
江南水鄉,富貴榮華之地,卻也不乏青樓瓦肆
這一天,滿腔鬱悶的侯方域和幾個同樣不得誌的“好友”,正在城中淩香閣,和當紅的玉玘姑娘,飲酒作樂,填詩作詞,共襄雅事。
明中後期,民間,尤其是江南,押妓成風,文人士大夫以此為樂,作風輕浮。
乃至於官場之上,也不以此為恥,反而當做風流倜儻的象征。
朱由榔本人對這種事情,其實是比較反感的,他倒是不在乎什麼敗壞風氣,這年頭的風氣再開放,也比後世差多了。
而是,這些“雅事”背後,所支撐的,是極為觸目驚心的人口買賣,這纔是他所不能容忍的,畢竟在他曾經生活的年代,買賣人口,那是最令人痛恨的犯罪之一。
當然,他也知道,移風易俗,絕非易事,而且國家未定,尚還冇有精力來應對這些破事,故而一直隻是先放在一邊而已,因為他知道,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事情,不僅僅是風氣而已,這些女性,絕大多數都是當初從各個天災**、餓殍遍地的地方流入,不來這裡,她們又能去哪?
自光烈三年,大明光複江南以後,侯方域一直都冇有得到什麼正經職務,仕途上無甚門路,這幾年也隻能和同樣際遇的狐朋狗友,每天青樓買醉。
其實朝廷不是冇給機會,之前他去南京衙門參加官員征聘,人家南直佈政使司,就給了他一個提舉常州府小學堂的正八品職司,但奈何人家瞧不上呢?
正說這一天,幾人在樓內觥籌交錯,不時互相打趣一番,或是起鬨行個酒令,捉筆作一兩句詩什麼的。
侍奉的玉玘姑娘自是賠笑在旁,或是撫琴,或是斟酒,還要附和吟誦兩句詩賦什麼的。
就在氣氛熱烈,大家都微醺迷醉,忘卻平時苦悶之時,卻隻聞樓下忽然漸起喧嘩。
喧嘩聲由遠及近,越來越大,不時夾雜著許多,不知是哭是笑的呼喊
引得正在堂中撫琴的玉玘姑孃的琴聲都被擾動,秀眉微蹙。
見美人遲疑,原本正在氣氛中的諸人突然被驚擾,自然是氣憤萬分
“哪裡來的俗人!大呼小叫什麼!”
侯方域氣勢洶洶,掀開旁邊紙窗,打算嗬斥樓下幾句
但隻當他剛剛掀開,整個人就愣住了,在座的所有人,都宛若木雕般定在遠處。
因為窗外,是一片喧嚷的海洋
蘇州城的大街小巷,到處擁擠人群,鞭炮聲、鑼鼓聲和哭笑聲,響徹一時,都向堂內所有人湧來。
“京師光複!韃子敗了!”
“韃子敗了!”
“大明勝了!北伐勝了!”
侯方域一時間,都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,氣氛陷入凝固
就在此時,身後卻是一聲斷絃傳來。
那位原本正在專心撫琴的玉玘姑娘,聽完窗外喧嚷之後,恍若失了神一般,都冇有察覺到繃斷的琴絃已將蔥蘢玉指劃出血痕。
失神片刻,竟是忽然泣涕出聲,美人垂淚,卻是愈加止不住,最後也不顧形象,竟是伏琴嚎啕大哭起來。
崇禎十一年,多爾袞、豪格、阿巴泰、杜度等人率大軍,由青山關、古北口,大掠關內。
西至與山西交界,南至山東濟南,方圓千裡內俱遭清軍蹂躪。
京畿附近以及山東等地七十城淪陷,近五十萬人口被擄掠一空,數十萬百姓慘遭罹難。
同年,山東大旱,人相食
這位玉玘姑娘,當時不過十歲而已,父母兄弟俱冇,隻一人,隨人流逃亡至兩淮,被人牙子看上,才倖免於難......
而整個蘇州府,整個南直,整個江南,乃至於整個天下,如她這般,又何止十萬、百萬、千萬?
堂中眾人,也都不是傻子,見狀多少也能猜出一二,隻是一時,居然不知道該說些什麼......
對於這個訊息,如果說北方士民們,由於曆史的慣性,還處在某種麻木與不知所措的話。
那當京師光複的訊息,以八百裡加急,迅速往南一州一縣傳播下去時。
所激起的情緒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。
喜極而泣的哭聲,彷彿如同瘟疫一般,伴隨著信使快馬向南行進的步伐,迅速感染了整個國家。
當訊息傳到江南,鞭炮聲、煙花聲、喧嚷聲、笑聲、哭聲,伴隨著祭祀亡人的嫋嫋香火,互相奔走的大紅拜帖,將一座座城市籠罩在內。
在這一刻,無論是何地出身,哪省人氏,持何政見,男女老少,從內閣、七部、府院,再到太學、國子監、中學堂、小學堂。
乃至於酒肆、飯館、店鋪,縴夫們揮汗的碼頭,小販們集散的市場,甚至勾欄瓦肆、青樓紅園。
人們第一次,像今天這樣,不分身份、階級,為同一件事,放聲歡笑,喜出望外。
尤其是青樓瓦肆,在這個年代,聚集於此的姑娘們,哪一個又不是苦命人?
江南無數繁華錦繡地,多少怡紅花粉鄉,這些婦女又是從哪裡來的呢?
自萬曆以來,天災**不絕,北方諸省,多少黎庶逃亡乞活,典妻賣女,多少血淚遺恨,哭聲震天。
而這一切,終於在這一天,畫上了句號。
劍外忽傳收薊北,初聞涕淚滿衣裳。
卻看妻子愁何在,漫卷詩書喜欲狂。
白日放歌須縱酒,青春作伴好還鄉。
即從巴峽穿巫峽,便下襄陽向洛陽。
而在北京光複後十餘日,纔在大軍扈從下,抵達北京城外的朱由榔,恐怕還對南麵此時已經開始沸騰的情緒一無所知。
作為大明天子,他卻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國家真正名義上的首都。
是的,雖然大明施行兩京製,但朱由榔哪怕在收複南京以後,已然隻稱呼北京為“京師”,而隻將南京稱呼為“行在”。
這不是遷都的問題,而是一個政治態度,是在隨時提醒所有人,真正的京師,還冇有光複。
而當他真正站在高聳的永定門外,看著跪滿一地的臣民,由於纔剛剛剪辮,看起來就像光頭一般,以至於不少讀書人,都用頭巾遮掩。
一杆略顯陳舊的明黃色龍纛,聳立在北京城永定門外,迎風獵獵,一如當初在桂林城頭、軍山湖畔。
都有些心情恍惚,乃至於眼睛濕潤
八年,從二十出頭,意氣風發,到現在為人父母,年至而立。
朱由榔此時的心情,有些像當年參加高考時,考完最後一科,走出考場的感覺。
但事實上,比那要強烈得多
畢竟這一次,他付出的不隻是努力,這一路行來,不知道多少人的鮮血、性命,多少肇慶、桂林、堯山、軍山湖,記憶模糊的麵孔,多少午夜夢迴時害怕、遺恨,兢兢業業、如履薄冰。
自己,賭贏了。
-